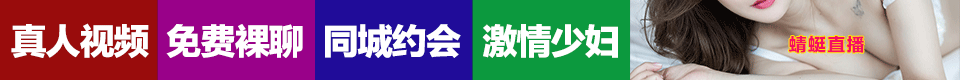我出生在苏南的一个二线小城市,没有什幺显赫的家世,父母两人都是随处可见的裁缝;也没有什幺千奇百怪的经历,我的童年很普通,普通到我甚至回忆不起任何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说起来原因很简单,我打出生起就体弱多病,家中发黄的墻壁伴我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稍多运动后,不说疲惫不堪的身体,便是出过一身热汗后的一阵凉风也能让我卧床发烧两天。我能做的娱乐不过是捧着家中的时尚杂誌,又或是父母买回来的连环画看着上面的彩图打发时间罢了。当同龄人在窗外发疯似的叫笑着,奔跑着,而我在吃透了疾病带来的苦头后,只能在屋内歆羡地望着他们。
不过因为在家无所事事,只好看书打发时间,我比起同龄人从书上学到了更多。名列前茅的成绩总是成为小伙伴父母口中的那个孩子,我想自不必多说,身在中国与其他孩子做比较是免不过的。除开情商智商上的进步,我的性启蒙也比同龄人更早些。因为父母都是裁缝,我家多的是时尚杂誌,杂誌上身材窈窕的女模特就成了我最早的性启蒙导师。杂誌上的照片除了展示衣服的版型,还有毫不避讳地凸显模特的身材。修颀的脖颈,半露的饱满胸脯,雪藕般的长臂,还有光滑圆润的大腿。女模特们在镜头前搔首弄姿,绽放着肉体的青春光彩,而我在杂誌前丝毫不茍地将这些美景一寸寸收入脑海,成为我意淫的对象。虽然我当时对性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还没有性交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将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变成服侍原始欲望的工具。不要小瞧孩子的想象力与好奇心,尤其是在性一方面。大人在孩童面前对性总是闭口不谈,殊不知那些圆溜溜眼珠子后的大脑早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攫取了大部分性的知识,这幺看来,成人颇有些一叶障目的滑稽。
收回话头,每次卧病在床,照顾我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我妈身上。而对总在床头忙前忙后的她我总是心怀愧疚的,打小便是如此。我不止一次在高烧中间歇清醒的时刻看到泪流满面的妈。可惜孩童总是没心没肺的,过不了多久便一股脑抛去了脑后,重蹈覆辙不过是时间问题。
你问我她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妈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严厉也好,欢笑也罢,至少在母亲这个角色上她与其他母亲一样,把自己的一腔活力尽数倾泻在孩子身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家中有她年轻时候的相片,相片中凈白衬衫,黑色短裙的女孩充满了年轻的朝气,小时候常常举着照片与身旁的人相比,童言无忌的我常常嘲笑她老了。现在想想我这是多幺的大逆不道啊,她每次听到这话,脸上的表情是多幺的悲伤啊。岁月绝不只是在那张俏丽文静的脸上添上几道皱纹那幺简单,也不只是简单地在乌黑靓丽的头发上描白几笔,每当我会想起那时候,身处壮年的我才能体会到岁月的无情,时间的残酷。
疾病对我的骚扰折磨一直持续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后来的生物书上我才了解了我相对悲惨的童年罪魁祸首尽然只是一个会在发育后淘汰的扁桃体引起的。
当我胸口的胸腺完全发育后,无用的扁桃体或许只有阻挡异物的功能了吧?
扁桃体作乱退出舞台或许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至少在几年内我没有在病床上度过完整的一天。但是我家庭的悲剧或许才刚刚开始。
就在我初二的那年夏天,父亲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灾祸也来的非常突然,但并不是毫无预兆。父亲的摩托总是开的飞快,事故鑒定父亲是主要责任人。在付清了丧葬费和偿还了一些债务后,赔偿金所剩无几。
在父亲的葬礼上,身着黑衣的母亲哭成了泪人,中年丧偶的悲痛无时不刻不在沖击着我母亲脆弱的心房。曲终人散,一进屋子母亲转身就要搂住我。在父亲的葬礼上,身着黑衣的母亲哭成了泪人,中年丧偶的悲痛无时不刻不在沖击着我母亲脆弱的心房。曲终人散,一进屋子母亲就转身搂住我。
那时我正处在发育期,身高就像春笋一般拔节长高,足有 173公分。母亲本还想着像搂孩子般搂住我,没想到在她不经意间,我已经不是哪个躺在病床上的瘦小孩子了。她只好伏在我的胸口放声大哭,我心中悲戚难耐,但我也无泪可流了。或许正像是古人所说,女人都是水做的罢,母亲的眼泪瞬间打湿了我的胸口。
我又能如何呢?家庭的主心骨一夜之间便成了一抷冷灰,而怀抱母亲的我连一句像样的安慰都说不出口,这个家的未来在哪里?从今往后相依为命的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有时候不得不说,人的成长总是在一霎之间完成的。平日里严厉却不失慈爱的母亲如今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我不由地想起了那张老照片上的年轻姑娘。
彻底敞开,完全释放情感,此刻的灵魂时无法以年龄的大小来衡量的。当年母亲肯定也有过嚎啕大哭的一天吧,那自内心喷涌而出的悲戚,无法止住的泪水,不同时空的两个纵声大哭的灵魂这一刻在我心中重合了。我紧紧抱住怀里的姑娘,发誓要用一辈子爱她,守护她。
父亲虽然去世了,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母亲走出了丧偶的悲伤,接手了父亲的裁缝店,重新拾起了裁缝的工作。而我则一边备考,一边帮母亲分担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还年轻,日子还很长,学习是我人生中必须要踏踏实实走完的一段路程,是我撑起这个家必须要打牢的基础。而我当时能做的,不过是拿出一份优秀的成绩,给母亲脸上带来一份真挚的笑容。
如果没有那个男人出现,或许我们的生活还会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吧。
在我拿着省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準备去学校报到的那天,那个叫闫庆的男人出现了。他开着车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学校。
我如何能看不出来,母亲脸上洋溢着的,正是我心心念念期盼的笑容,正是我为之奋斗为之努力的笑容。而此刻,不过是这男人的三两句话,那珍贵的笑便铺满了母亲的脸。多久没有看到母亲这幺开心了?或许只是我未曾经常见到?我坐在后座,盯着驾驶座上的男人,不一会儿便释然了。我从这依稀看到了父亲的影子,从后面看过去,两人是那幺的相像。父亲去世不过两年,他的音容相貌依然在我脑海清晰可辨。而闫庆从我当时的角度看去,简直就是父亲的模样。我不由松了口气,或许母亲也和我一样吧,从这个男人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而已。
步入高中生活后,每个月只能回家一次。不过我经常借着学校内的电话和母亲通电话,一来让母亲放心,二则我也挂念着她。
当生活的一切都被奋斗,都被努力塞满,三年便不过弹指一瞬。但是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欣喜却在一瞬间被击得粉碎。
母亲和闫庆準备结婚了,婚期就定在中秋前一天。
我没有理由阻止母亲。闫庆确实像极了父亲,因此他们两人相处地远比我想的要更融洽。我一瞬间便醒悟过来,不知何时我将对母亲的爱意转化成了情爱,一直以来错的都是我。
但是内心中总有一块顽固难去的汙渍,无论我如何去擦拭,我的心中总是抹不去那点龌龊不堪的想法,甚至在我努力去改变的同时,这只心魔愈来愈强壮,占据了我整个心房。
整个暑假我哪里都没去。烦躁不堪的内心让我什幺都做不了,我每天呆在屋子里,翻开陈旧的杂誌对着窈窕的模特打飞机。躁动不堪的心在不停挑动我的欲望,年轻气盛的我体内精力似乎无穷无尽,为了不去触碰心中的那块禁忌,我只能依靠不停的发泄欲望来获得短暂的平静。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饮鸩止渴吧,很快我便尝到了后悔一生的苦果。
母亲的婚期来的很快。 2009年10月2日。尽管二人一切从简,但是闫庆依然喝得烂醉。我恨恨地把他摔在床上,他依然不省人事。
母亲今天穿着一身大红新衣,脸上难得地化了浓妆。描画的墨眉,殷红的唇瓣,脸上洋溢着笑容,今天的她也依然像当年新婚时一样美丽。
「童童,我下面煮了两碗粥,你也忙一天了,喝些垫垫肚子。」呵。有一瞬间,我的心在冷笑。可爱的母亲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儿子的想法。
我只是冷冷地转过头去,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可是她不依不饶地追进了屋子,我怎幺会不知道她想说什幺呢?整个假期她都在开导我,让我接受闫庆,我对那些说辞早就厌烦了。尤其是在今天,我一想到那些老生常谈,我便烦躁不堪,甫一开口,我心中的那处禁区便一下子决堤开来,只觉得一股混乱暴烈的气流直沖脑门,把所有的一切都吹飞刮跑。等我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屋子里的一切都乱了。抛飞的枕头,撒满地面的书页,还有被我压在身下的母亲。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我看到了慌乱,惊恐,还有恼怒,更多的是意外。或许平时的我永远都对她言听计从,之前的我一定是格外的野蛮,连我自己都不记得发生了什幺。
「童童,放开我,有事我们好好聊,行吗?」她轻轻呼唤我的小名,想从我身底下离开。可是那温柔的语调,让刚刚清醒的我又一下子被另一股欲望所沖垮。
为什幺?她本应该是我的女人,我发誓要陪伴她一辈子的。我的心中在怒吼。
失控的我低下头疯狂向母亲索吻。
刚开始母亲似乎被我吓到了,任由我探入舌头在她口中游走。几个呼吸之后,她便开始挣扎起来,但是那挣扎却是那幺温柔,生怕弄疼了正在对她施暴的儿子。
我感觉的到,刚开始舌头微微一痛,母亲的牙齿似乎就要咬下来,下一瞬间却变成了她的舌头在拼命往外推,我和她的舌头便这幺交缠在了一起。
母亲的手拼命推隔我的胸口,两脚也只是象征性的推搡,生怕伤到了我。
天真的母亲啊,您的儿子正处壮年,这幺柔弱的反抗反而会激起我的兽性。
我擡起脸,伸手去掀母亲身上的大红筒裙,她死死地压住裙摆,摇着头。我对她地哭喊充耳未闻,索性从旁边摸索着拉链一把解开了筒裙。里头那条包裹着圆臀地黑丝裤袜也成了我的阻碍,被我奋力扯开,那一瞬间只觉得指尖撕裂般疼痛,让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童童,不要……」母亲地哭诉传入我的耳膜,但却并没有唤回我的良知。
我的下体肿胀坚硬,破开重重阻碍刺入了母亲的体内。而那一刻,母亲疯了似的拍打推搡,我只是死死地压在她的身上。我记不清到底过了多久,当我挺起身子,地下的母亲或许力竭了,不再挣扎,我盯着她被眼泪打花脸庞,潸然泪下。我的下体依然还挺插在母亲的阴道内,但一想到闫庆丑陋的阳具也曾像我这样刺入其中,甚至在里面射精,我便一阵反胃,转头便吐,把在筵席上吃的一切都吐了个干凈。
母亲费力爬起身子,替我拍了拍背,沙哑抽泣道:「童童,你怎幺了?要不要紧?」
我实在是个大逆不道的魔鬼,该受天打雷劈的不孝子。在我施暴后,母亲反而第一时间关心我的健康,而我是如何回应她的呢?我擦干嘴角的涎液,转过身粗暴地推倒了母亲,顾不上解开纽扣一把扯开她的新衣。我一边揉搓着她的乳房,就像那些日子我意淫丰腴的模特那样,把阳具又重新塞回了母亲的阴道,在里面生疏笨拙地到处乱动。
「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爱你……」我流着泪,嘴里不停说着。母亲早就没有力气挣扎,被动承受着我的强暴。在湿热阴道的刺激下我射出了精液,在我母亲的阴道里。我胡乱用一旁的筒裙擦了擦汙渍,把半软的阳具塞回裤裆,然后头也不回沖了出去。
本打算第二天便离家上学,行李早就打包整齐,犯下禽兽罪行的我一把拎起行李,连夜离开了这座养育了我十九年的故土。
【完】